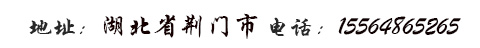光影青春大学生电影节回顾专题郭帆整个世界
|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北京国际电影节·第27届大学生电影节将延期举办。虽然无法与大家共赏电影新作,但我们尚有往日岁月可回首。自年至今,大学生电影节始终坚持“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拍、大学生评”的特色,秉承“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的宗旨,为新生代电影人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也见证着新生代电影人的成长和发展。 流火七月,大影君特别邀请大影节的老朋友“返场”,与网友们分享创作故事,回望大学生电影节与中国电影的共同成长之路,让我们一起回溯光影,探寻影片中的文化基因,细品镜头下的人生百味。 郭帆导演的创作故事分享 本期回顾的嘉宾是郭帆导演。年,郭帆导演的《同桌的妳》获得第21届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大奖。年,其执导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获得第26届大学生电影节“大学生注目单元·最佳影片”。该片树立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全新标杆,是中国电影一次成功的类型探索和实践,彰显了中国电影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同桌的妳》, 郭帆导演在接受大影节采访时谈到:“大学生电影节对于我个人来讲情感深厚。从《同桌的妳》到《流浪地球》,大影节一直给予了很多的褒奖。我特别珍视这个奖,因为这是大学生的奖,大学生就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他们能够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主流的。能够被他们认可,我是很开心的。” 郭帆导演也为大影节送上了祝福:“特别希望我们的大影节可以越办越好,希望有更多精品的、有社会效益和社会意义的影片,出现在大影节上。” 《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讲述了太阳即将毁灭时,人类在地球表面建造出巨大的推进器,带着地球一起寻找新家园的故事。然而,宇宙之路危机四伏,为了拯救地球、让人类能在漫长的年后抵达新的家园,流浪地球时代的年轻人挺身而出,展开争分夺秒的生死之战。 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硬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成功刻画出了平凡英雄的人物群像,将中国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融入“带着地球逃离太阳系”的宏大叙事,从渺小个体的视角出发,纪录人类自我拯救并守护家园的史诗征程。不同于好莱坞式的“超级英雄”,《流浪地球》展现出的是中国人依恋故土的家园情怀和甘愿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以“为人类计”的大格局和大气魄投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主动背负起拯救同胞使命的刘培强与主张保留“火种”的MOSS在思想上进行交锋,人性光辉在感性与理性的戏剧化冲突之中得以彰显。 《流浪地球》剧照在本期访谈中,郭帆导演与我们分享了创作过程中的许多思考。 大影君:《李献计历险记》、《同桌的妳》和《流浪地球》题材跨度很大,您是如何驾驭类型迥异的影片的? 郭帆导演: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可能跟类型关系不大。因为从小我决定想去当导演,就是想去拍科幻这个类型。所以你会发现,即便是第一部片子《李献计历险记》,里面都有很多关于科幻的设定和拍法。只不过当时我个人的经验,包括我个人的成熟度还不够,包括我们对科幻这个类型的认知,以及当时的工业化程度,可能没有办法很好地完成科幻这个类型。 但是我觉得我会一直去坚持去做科幻。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同桌的妳》里面也有一些科幻的设定,只不过后来都拿掉了,因为实在是不太符合这个类型。所以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是一直在去选择科幻这个类型和方向,并且会一直坚持下去。 大影君:您大学学的是法学,然后后来做导演,专业身份对创作有什么帮助吗? 郭帆导演:有帮助,会帮助你去从别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其实我们会发现不同行业中的人,大家的基础逻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商业上有商业的逻辑,投资人有投资人的逻辑,互联网有互联网的逻辑。那么做电影,做文化是有它本身自己的一个逻辑。 法律跟这个也完全不一样,但是会让你从另外一个视角去观察所要从事的行业。法律会让你的思维多一些逻辑性、更加条理。这也让我们在真正做完《流浪地球》之后,发现我们在工业上走了很多的弯路,然后会有很多的坑要填,所以才会想到之后要去梳理电影工业化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跟学法律是有关系的。 大影君:时间始终是您影片中的表达重点,您的时空观是怎样的?在进行时空塑造的过程中有哪些独特设计? 郭帆导演:这是个哲学问题啊。时间是我们感受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我本能的会喜欢去探讨时间,之前我没有发觉这个问题,是后来有几个影评人跟我讲,你有一个母题,你的母题一直跟时间有关。所以在整个影片的展现上,你会发现它偏向于某种编年史的方式,去讨论时间。 当然就我个人对时间理解来讲,可能我觉得时间并非是我们今天所感知到的,它是一个线性流动式的一个状态。我个人可能更偏向时间是静止的,只是我们的感受是流动的。类似于你可以把时间理解为1秒钟24帧的一个动态的影片,只不过它的帧速率远远不是24,它可能会很高,只是我们无法观察到这个间隙,是这么一种感觉。 大影君:您在作品中使用过动画、影像等多种媒介手段,您为何会选择跨媒介叙事? 郭帆导演:想多做一些形式上的尝试,只不过到今天会明白,那些都不是电影本身,因为电影的核心是人跟情感,你拿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都可以。是因为一开始太年轻,总是特别容易被各式各样的表达形式所吸引,然后会去研究,甚至去想要不要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我觉得到今天让我再去讲这些形式的话,我会考量它的性价比,看哪种形式更容易表达我们的人物跟情感,就是外部的包装、内核和这个影片的灵魂契合才是最重要的。 大影君:《流浪地球》的剧情在原作小说中占比较小,人物故事线是怎样打磨出来的? 郭帆导演:《流浪地球》的小说,你要如果这么讲的话,应该是小说中的剧情占比比较小。但是对于《流浪地球》这部电影来讲,小说的世界观几乎就是这部电影的全部。因为这部的世界观,是大刘老师去建立的,并且有明显的刘慈欣的一个风格。所以我觉得是大刘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巨宏大的一个世界观,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观中去选择我们去看待这个里边的人物的视角。所以我觉得它并不是跟小说关系不大的那种感受,而是其实它就是脱胎于小说。 大影君:您认为灾难类、科幻类宏大叙事需要怎样的支点? 郭帆导演:还是人跟情感。因为电影的核心就是这个东西,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类型,什么样的场面。灾难也好,打的科幻或者玄幻奇幻。你首先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里面的人物。相信这个里面的世界。只有这两点,相信了之后,观众他会跟着你的角色去投射他的情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做电影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 大影君:《流浪地球》重在塑造英雄群像,人物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与西方科幻作品表达不同,您怎样看待这种“科幻时差”? 郭帆导演:这个不叫时差,应该是跟文化有关系的。至少在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世界上,大家还是以国别相分的,在国别相分的情况下,各国有各国的文化。那么其实我们在去做《流浪地球》的时候,最核心的还是要服务于中国的观众。 我们没有太考量西方观众文化上的感受,我们尽量符合中国文化,能够让中国观众看上去有亲切感。其实解决的问题依然是人跟世界的真实度。只有让观众相信,这里边的人就像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一样,相信我们描绘的这个未来世界,就是我们正常发展了50年之后的世界。只要相信了这两点,故事往下推进就有支点。我觉得,支点其实还是人文情感。 大影君:《流浪地球》是怎样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故土情结的? 郭帆导演:这点是确实和西方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在西方看到,甭管是科幻片也好,还是超级英雄电影也好,大部分是以个体为单位。超级英雄基本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我们展现的方式是用更多的人去展现。 很多情况下,这些人在平时都是普通人,在关键的时候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决定、选择和行动,让他们成就了英雄。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平凡即英雄”的这个点。那么一个又一个的平凡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是超级英雄。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去展现,这个方式其实刚好展现了我们特有的一个集体主义的状态。如果把这种状态放置全球的话,那其实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我们与环境之间,整个世界,呼吸与共。 大影君:影片中有哪些部分让您留有遗憾? 郭帆导演:这个太多了,遗憾太多了。这个片子的满意度,就我个人来讲,可能我给自己打70分都不到。但是如果是整个团队来讲,我会给他们打分。这是台前幕后人大概花了4年时间,拼尽全力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我对整个团队,每一个人都非常感动,也觉得他们付出了巨大的辛劳,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前段时间我还真的重新看了很多遍《流浪地球》,会发现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出自于我当时的一些判断和决定。这部影片拍完之后,我才能够感受到,从导演这个角度来讲,我好像是摸到导演这扇门了,但我还有一只脚没有跨到这个门里边。就好像你掰开了一个门缝,通过门缝能够往里看,里面有好多导演,我只是刚刚摸到门的这个感觉。 大影君:《流浪地球》被评价为“开启了科幻元年”,但迄今为止尚无其他优质科幻作品诞生,您怎样看待中国科幻的前景? 郭帆导演: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科幻元年。什么叫科幻元年?我觉得它是一个历史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看有多少部科幻片可以在同一个历史年代去集中出现,就类似于今天的好莱坞的一个状态,每年都会有若干部优秀的科幻片出现,那么科幻片这个类型才能被确立起来。 但这个类型被确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时间线上去找这个原点是在哪,其实只有一部《流浪地球》或者是《疯狂的外星人》,这么两部片子是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件事情的。之后我特别期望的是有一部又一部优秀的中国科幻片出现,才能够构建起中国科幻类型。当这个类型被建立之后,我们再去找这个时间线,那个时候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个原点。 大影君:未来您会继续创作科幻类型片吗? 郭帆导演:在之后应该在很长一段时间吧,我包括我们整个团队都会致力于做科幻这个类型,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和我们同行一起,去出更多的科幻片。首先我觉得大目标是要把科幻类型建立起来。 大影君:您认为中国电影工业化程度如何,与国外相比我们还有哪些短板?您在创作《流浪地球》的时候有哪些体会? 郭帆导演:我们现在在国家电影局的指导下,然后跟北京电影学院合作,然后正在做电影工业化的一个梳理工作。当我们真正开始做这个处理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标准层面上的制定,远远落后于好莱坞。 比方说我们现有的标准,大概是46个,而且这些标准多数是在整个产业链的放映端。所谓的放映端就是指我们在影院中银幕的尺寸大小、亮度、声音的响度这些东西。那真正在制作跟创作环节的标准,我们几乎是零,那好莱坞是大概多个,然后以每年50个新标准去递增,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直观的差距。 简单来讲,就像我面前的这台摄影机一样,你把它拆开之后,你会发现里面可能会有1万个零件,每一个零件都需要标准,而且都需要命名。只有把标准和命名处理好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把它通过一个流水线组装起来,而组装起来这个过程其实是流程。我们其实是需要一步一步地重命名、定标准到疏理流程,这个过程才可以把我们的工业化一步一步地完善起来,所以它是一个长期计划。 其实我们定了三个五年的计划,大概需要用15年时间,去一步一步地完成这些事情,然后最终通过国家标准委员会的形式,去认定这些标准。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这15年的梳理过程,可以有一个教材出来,在之后的专业性的高校中,学生们可以学到这些流程上的内容。 我们还会做一个可执行、可使用的软件,在实际拍摄中,同行们就可以使用这个软件,使用这个流程。当他们发现问题的时候,又可以反馈给我们,我们再不断地去迭代。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整个过程中的所有部分都是免费的,希望它是一个基础的基建,是电影工业的一个基础设施。就像铺路一样,我们希望能够在电影局、在电影学院的共同支持下,共同去完成这件事情。 大影君:疫情期间,电影创作和放映都遭遇了极大困难,您认为电影行业如何才能走出“寒冬”?您对电影工作者有什么建议? 郭帆导演:第一,特别期望整个行业中,特别是在外部来讲,很多投资人、出品人,资本层面上要对这个行业有信心。我们只是遇到了短暂的一些危机,这个危机是来自于疫情,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控和不可抗力的事情。但是整个电影行业来讲是一个蓝海,是一个朝阳产业,所以希望更多的投资人跟资本层面能够保留信心,多有一些耐心,不要离场。 第二个层面,就是作为创作者来讲,我们也要对我们自己的行业有信心。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扛过这一段,不要说轻易地就转了另外一个行业,这个行业中的最核心的还是人。 第三个层面是对于观众来讲的,我相信如果资本,如果我们的创造者不离席的话,也多给我们一点耐心。然后希望疫情过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更好的优质的电影反馈给观众。 《流浪地球》剧照 在本次访谈的结尾,郭帆导演将《流浪地球》中的一句台词赠予当下的电影人们:“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郭帆导演希望中国电影人热望不熄、初心不易,携手并进而不轻易离席言弃,与电影一起共同存在下去,如刘培强等平凡英雄一般,坚守住我们的共同精神家园和理想阵地。 (文中剧情简介、剧照来源于时光网)撰稿:孔媛设计:叶大扬、曹敏华外联:夏之睿栏目主编:孔媛审校:蒋希娜、陈寅、何昶成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ianyingjiea.com/dyjzt/8653.html
- 上一篇文章: 征稿大学生电影节middot国际
- 下一篇文章: 第十二届大学生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