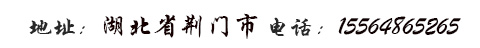入围一个导演的理想与现实
|
导演沃纳·赫尔佐格说过:“我就是我的电影。”一个导演的审美志趣往往在他的电影里展露无遗,而在起步阶段的青年导演,更倾向于将个人生命体验投射到作品当中。 带着对青年导演创作状态的好奇,FIRST与《智族GQ》杂志一道,去往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场景中,试图在他们的生活里找到蛛丝马迹,探寻他们的作品与个人的关系。 01 《动物方言》雷磊导演 ——如何成为“完全体”? 在北京的一个胡同深处,采访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看着举起的相机,雷磊导演一愣,对着镜头问:“我能戴上帽子吗?戴上帽子我就是‘完全体’了。”一句话惹众人大笑,瞬间胡同里的气氛变得轻松活泼。 胡同里的小屋内堆满了雷磊的各种老照片拼贴,他还打开小方桌给我们看他用橡皮泥捏成的各种家庭人物——爸爸、妈妈、自己……他热衷于用Ready-made的图片创造出新的艺术价值。 一年里他一半时间在中国,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剪纸、拼贴和制作动画,或者回到江西老家陪伴家人、与好友出游;另一半时间在美国,在加州艺术学院里教书获得收入以维持生计,平常也会去逛各色展览,与挚友、学生共同谈论艺术,亦或是跟朋友们玩音乐,体验美式休闲娱乐。每年奔波两地的经历,也会让雷磊思考民族差异、身份认同等这样的问题。 摄影 沈伯韩 02 《慕伶,一鸣,伟明》黄梓导演 ——拧巴的两代人 在北京通州运河边,我见到了《慕伶,一鸣,伟明》的导演黄梓。刚过三十的他,已是一头银发。这里是他晚上经常散步寻找灵感的地方,亦如他在广州时,焦虑的时候就会在家的附近走一走,排解心中忧闷。 在采访过程中,黄梓不善言辞,说话慢吞吞,常常停下来左右思考问题。不过交流之后,你会发现,在偶尔的沉默间,他一直试图疏理自己的逻辑。 高二结束,黄梓决定离开父母,去往美国西海岸求学,那时,他还不知道电影是什么。黄梓说,在高中时期,强烈的自我意识,让他拥有了关于世界的不同看法。而这些看法,或对或错,让自己与父母产生了更多争执。有时候,因为彼此的执念,不惜恶言相向,试图迫使对方闭嘴。那时的他,萌生出对自由的强烈渴望。 出国几年之后,在读电影制作MFA课程的黄梓,不顾父母反对,决然退学回国,一如当初离开家那般。不久,黄梓的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在父亲生病时,黄梓放弃了前往布拉格电影学院深造的机会,这次,他没有再选择“自由”,在家拿起摄像机,陪伴着父亲。 在黄梓的创作阐述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父亲的死亡是不可逆转,那么之前我远离父母而获得的七年“自由”意味着什么?我中止学业提前归国,这却在冥冥之中让我得到了陪伴父亲走完他最后一段人生的机会,这种命运交织的抉择又意味着什么? 黄梓的母亲至今仍耿耿于怀他没去捷克,父亲去世后,黄梓觉得他与母亲二人的生活状态变得尤为重要,如何与母亲相处也是目前一直困扰他的问题。 摄影 郭旭宏 03 《平原上的夏洛克》徐磊导演 ——伫立于乡土社会的守望者 北京朝阳区一安静的小区内,零零散散的几个大爷踏着慵懒的步子左晃右晃,身边跟着的狗尾巴左摇右摆,楼上徐磊导演早已便装等候。 当徐磊谈到剧本一稿20多天写完、片子20多天拍完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应该是这波青年导演中最顺利的一个,其实不然。原剧本的设定是一父一子两代人的矛盾,但选角过程并不顺利,找来的演员在故事环境中都显得极不协调,无奈之下由自己的父亲亲自上阵。组建主创团队也并非一帆风顺,剧组30多人唯独缺少服装部门,每天拍摄完后徐磊还得自个儿清洗所有演员的服装。 徐磊说自己接下来的创作将会继续聚焦于华北平原,展现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隔阂和冲突,这也源于徐磊对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原有生活状态消亡的反思,亦是在审视自己的生活经历:生于北京奶奶居住的胡同里,七八岁去往河北父母家,成长在华北平原上,对于父母这种集体生活、人情社会中的办事逻辑也有着自己的观察和理解。 摄影 郭旭宏 04 《马赛克少女》翟义祥导演 ——北漂青年成长记 写作剧本的时候,翟义祥导演常去的地点是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的网吧。因为夏天炎热,房间空调不太制冷,他就去网吧开个晚晚场写作,而且一般都是晚上十一二点开始,一直写到凌晨三四点或者四五点才回家。 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创作,翟义祥北漂了很长一段时间,住遍了北京的各式各样的出租屋——地下室、隔断间以及单间,去到影视公司里做视频剪辑的工作。他说,这是一个有趣的经历,也是他成为导演前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谈起拍摄这部电影遇到的困难,翟义祥说自己是一个记不住困难的人,唯独记得有场令大家头疼的雨戏:为了消除喷洒的痕迹,使电影画面更好地呈现,现场制片提议用水管接满淋浴头制造真实感,但在一个纵深近百米的巷子里去实现的难度很大。剧组买光了全县城的淋浴头并用各种管子焊接,因为水泵的压力问题以及接头的地方一直在出问题,工作人员连续十几个小时未休息,终于在尝试了无数遍后成功了。但附近有些住户不允许剧组在他们的墙上钉管子,为了安抚居民,剧组买了礼品蹲在住户家,吃饭喝酒聊拍电影的不易,到最后甚至有户人家都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剧组人员!两天的时间内终于拍摄完成,雨最终下得很真实。翟义祥也意识到:现实中很简单的一个自然场景,在剧情片里要花费很多的功夫去呈现。 摄影 郭旭宏 05 《离秋》汪崎导演 ——不断追问来处 汪崎导演,留着一圈山羊胡,带着一副眼镜,穿着随性。作为第二代移民华人,从小在日本长大,汪崎也面临着身份认同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许多上海人远赴日本东京打工养家,回顾起自己当时一起长大的华侨圈子,汪崎决定用电影的方式来记录这段跟自己相关的移民家庭往事。 汪崎虽然拍摄过许多短片参展获奖,但他目前依然是靠着在日本和上海两地工作(包括不时兼职日语翻译)来挣钱拍片,汪崎坦言“专职做电影生活太难了”。在之前的创作阶段,汪崎是在上海写作剧本。平时写作疲惫,汪崎排解烦闷的方式就是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闲逛,偶尔在路边小卖部里买点东西,然后回家继续创作。 因为是合拍片,工作人员当中有中国人、日本人和西班牙人,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难免会有摩擦。又因为自己独立制片组建主创团队,成本的原因也限制了拍摄时间,只得控制在一个月内完成电影拍摄。但拍摄处女作长片的困难远不及此,拍摄场景也是一个着实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日本的房子比较小,拍摄器材难以伸展,演员调度难以展开,于是汪崎和团队决定将内景放在上海,并在上海搭了拍摄棚,将外景放在日本;但是外景拍摄遇到的问题也相当多,有些街道不允许拍摄,有些街道只能拍摄道路的一边。汪崎和团队当时在每个区都申请了拍摄,和拍摄街道上的每个商铺都打好了招呼,但是依然会有居民报警,制片人只好跟去警察局处理情况。因为拍摄的各种限制,电影多少留有一些遗憾,但这也许就是青年电影人在起步阶段都需要经历的阶段吧。 摄影 《离秋》剧组人员 06 《第一次的离别》王丽娜导演 ——书写故乡诗篇 胡杨木做成独木舟,行驶在塔里木河上,驼铃声从塔克拉玛干腹地传出,千年的胡杨树叶沙沙作响,这就是王丽娜导演度过童年时光的地方。藤架下,王丽娜导演的身旁,民间艺人弹奏起属于那片大地的乐音。 对于电影创作,王丽娜想要通过《第一次的离别》来把自然给她最直接的感受和时光留下的印记尽可能真诚可信地呈现。五年前,王丽娜想拍一个关于自己家乡的片子,调研期间读到了影片主人公艾萨写给妈妈的一篇作文,被艾萨对妈妈的爱深深打动。随后王丽娜去了艾萨的家里,阳光洒在木质的架子上,艾萨光着脚丫,正抱着一只小羊羔给他喂奶,小羊羔不听话,他就用自己的嘴去亲吻这只小羊羔——这个画面也唤醒了王丽娜童年时代的记忆。不仅如此,她的中学时期也和片中的艾萨一样,远离家里去住校,是人生的第一次的离别。但当王丽娜再次回到故乡,那种陌生又熟悉的气息,使她开始和生活的土地互动,和自己的经验互动。 谈到拍摄过程中的困难,《第一次的离别》聚齐了“老人、孩子、动物”这三大难,而且演员都是从未有过任何表演经验的素人。王丽娜为了能让家乡的人民在镜头前自如地表现,进行了半年时间的田野调研和一年的纪录片拍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和这片土地上具体的人镶嵌在一起,了解他们的生活、性格、说话的语态方式、文化习俗等一切”。 拍摄的经历对王丽娜来说也是一种对自我的发现,对由纪录片进入影像世界的她来说,作品绝不是产生于自我幻想之中,而是产生于“我”与“世界”相接的地方,让自己对现实和日常生活保有敬畏之心,也让自己回到自己第一次离别故乡的地方,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向。 摄影 徐沉沉 距离媒体嘉宾注册通道关闭仅剩6天 媒体报名 无论他们去到什么地方,那里的未来都会改天换地 距离电影节嘉宾注册通道关闭仅剩6天 电影节嘉宾注册 无处安放的热情,从这里开启 距离第13届FIRST影展开幕还有16天 竞赛入围影片、竞赛评委会阵容 这份“破纪录”的片单将送到谁的手中? 展映排片明日公布 ▼点击阅读原文,观看本届影展入围影片预告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ianyingjiea.com/dyjhb/8107.html
- 上一篇文章: 第70届柏林电影节公布竞赛名单蔡明亮洪
- 下一篇文章: 幸福蓝海疫情下的戛纳电影节公布片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