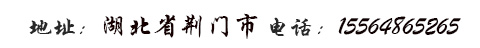学校不该是个什么组织
|
(一)碎片化时代。 现代人并不是没时间,还是过去的二十四小时,时间,究竟去哪儿了?是被无数琐事切割成碎片。尤其是班主任。从早晨到深夜,从周一到周日,白加黑,5+2,所有时间被各种检查、谈话、开会、量化、验收粉碎成以分钟为单位的细小碎片。 古人用一生做一件事,曹雪芹用半辈子写红楼,司马迁用一生修史记。今人用一生做很多事,却大多是无用的琐事。古人生活节奏慢,时间大多属于自己,今人生活节奏快,时间大多属于别人。现代人,尤其是单位人,已彻底丧失了认真做一件事的可能。 当然,周树人先生说:时间是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还是有的。尴尬的是,现在的海绵,都是小块海绵,硬挤出来的水,也只是口水而已。时间碎片化,叠加信息过载的洪流,加剧了思考的肤浅化。 碎片化的时间使人们无法再深入整理信息和资料;信息的唾手可得又使人们丧失了整合思维的动力。碎片化时间必然带来的是碎片化思考。更重要的是,刚开始展开思路,似乎有个好的idea,却马上又被各种突发状况打断,处理完杂事后,那个“好的idea”早已灰飞烟灭。恰如一个情节跌宕的好梦被一泡尿憋醒,上完厕所再进入睡眠,那梦是如论如何也找不回来了。 一种尴尬:领导说你们要认真备课,却同时安排无数的杂事切碎你的时间,让你无法集中精力思考。一种吊诡:老师说同学们要有创新能力自主能力,却同时不允许学生有“参考答案”以外的自由思考。一个疑问:一个背“标准答案”的民族能凤凰涅槃基因突变,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大国吗? 能坐下来完整思考,完整码字的机会越来越少。当然了,碎片化的时间也是可以做好些事情的。比如,翻几页书,找个学生聊几句,记下一点零星的思考。只是,要完成系统性、深入性的思考,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二)组织化生存。 人类与动物有好多区别,其中一个是: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组织化的动物。动物也有所谓的“组织化”“社会化”生存,比如蚂蚁、蜜蜂、狼群等。但动物的“组织化”生存与人类相比,其性质、规模、种类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尼采说:只有上帝和野兽是孤独的。人类既非上帝,也摆脱了野兽。完全、纯粹孤立的人类个体是不存在的,几乎所有的人类个体都分属于不同类型的“组织”。即便是游离于社会边缘的乞丐、流浪汉、拾荒者,其实也必须与各种组织发生联系。因为,离开了整个社会组织的各种供给,所谓孤独的“流浪汉”,根本就无法独立生存。传说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所谓“桃花源”,在现代社会,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罢了。 人类历史,不但是文明的演进史,同时也是组织的演化史。文明,就其多数成果而言,都是组织分工协作的产品。 单个人集结成各类组织,是因为1+1大于2,1+1+1大于3甚至大于10。分工与协作催生了各类组织,组织内分工的细化解决了独立个体无法完成的艰巨挑战,组织内人与人的分工协作、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在简化了劳动的同时,极大提高了组织整体的总生产效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举过一个经典例子(即便到了今天,比尔盖茨还常引用此例子。):制针工场把制针的工序分解为十八个工序,分别由十八个工人协作完成,一天可以生产四万八千枚钢针,平均每位工人每天可以生产几千枚钢针,该工场的产品可以供应全世界。如果所有十八道工序由一位熟练工人独立完成,那他一天连二十枚钢针也搞不定。 一枚小小的钢针尚且如此,零部件繁多的手机、汽车、高铁、飞机等复杂工业品,如果不是由全社会的复杂分工完成,而是交给几个熟练技师独立生产出来,已经不是效率低下的问题,而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至于修路架桥、冲锋陷阵、交通秩序、拍摄电影……等等所有社会行为,没有各类组织的分工协作,整个社会根本无法运转哪怕一天。 (三)组织的异化。 组织不是万能的。一切组织都有如下两大弊端:人的异化是组织的第一个副产品。能量内耗是组织的第二个副产品。组织规模越大,分工越细,人的异化越严重。组织规模越大,层级越多,能量内耗越严重。 还是亚当·斯密,在同一本书又说:“当一个人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一只扣针的十七分之一或一只扣钮的十八分之一的时候,见识必然更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切商业国家,下层阶级人民都非常愚笨。”诗人席勒指出,随着工业革命导致的分工,“人类成为永远束缚在个别小部件上的人,本身也成了部件。”马克思多次分析了人类异化现象,他指出异化的实质在于,“人类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与人类对立的东西。”马克思晚年在《资本论》中指出:未来社会将是“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至少从目前看,马克思晚年的构思可能还很遥远。 所谓专家,就是“在越来越少的问题上知道的越来越多,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知道的越来越少”的文盲而已。 一个传统农民,到哪里都可以继续做一个传统农民。一个现代农民,脱离了社会协作根本无法种植谷物。一个码农,离开了特定行业的特定岗位,几无谋生技能。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载:有名士在京师买一妾,自称曾在太师蔡京府中后厨中做包子。某日,命该妾做包子,答曰不能。曰:在后厨包子部门只负责切葱丝,别的不会。 看来,人的机器化、部件化、异化不是工业社会的专利,而是自古亦然。 随着组织层级增多,组织的协作成本、管理成本日益升高,信息耗散现象日趋严重。下情不能上达,上令不能下行。大量的员工精力不是用于完成任务,而是浪费在组织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扯皮内耗上。 中小型组织发展为巨型组织后,组织内部的分化出各类小型组织,这些小型组织为了本部门的局部利益,各种拼抢资源和责任推诿,无视甚至伤害整体组织的健康,如同人体身上恶性生长的肿瘤一般,最终导致整个组织的“无组织化”。 物理学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描绘了一副黯淡的结局:宇宙万物发展的总趋势是趋于“热寂”。部分组织强化“秩序”的结果,是更大规模组织的“无序”。 有不少公司、学校、单位在规模较小时,执行力很强,向心力很强。一旦做大,反而传染上了“大企业病”,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人心涣散,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其他组织击败。 从组织演进的角度看,历史上太平天国的悲剧、前苏联的解体、国民党的溃败、计划经济时代国企的破产,都是组织凝聚力涣散、组织内耗严重、组织执行力低下的结果。如何保持组织的凝聚力,使组织永葆活力,是一切组织面临的永恒难题。 (四)组织的凝聚力从何来? 问题来了。大到国家、民族这样的抽象巨型组织,中到商业公司、政府机关的常规实体组织,再到学校、班级这样的具体微型组织,决定他们生命力、凝聚力的秘诀究竟何在? 按照组织的类型,人类归属的主流社会组织大约可粗略划分为以下几类: 政治组织,如ZF、军队、警察、法院、政党等,产生于阶级社会;提供管理和秩序,维持组织运作的基本逻辑是权力规则。经济组织,如作坊、工厂、公司等,工业社会里飞速扩张;创造物质财富,凝聚成员的基本逻辑是经济利益分配。精神组织,如教会、寺庙、学校、学会等,负责文明传承和灵魂抚慰,团结成员的基本方法是信仰和情怀。血缘组织,家庭、家族、村落。家庭是最古老的社会化组织,这是人类存在时间最长,也是最顽强的基本社会组织细胞。血缘组织的的凝聚力向心力,与其说缘于血缘,不如说是依赖于亲情感情。此外,还有其他的非主流边缘组织,如帮派类、某某协会之类。 参考答案:任何一个想长葆青春长盛不衰的组织,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公司企业,抑或是学校团体,甚至是最古老的家庭,边缘化的地下帮派,必须兼顾好凝聚组织的四个要素:权力运行、利益分配、情怀信仰、亲情人性。 仅有权力压制的组织管理是愚蠢粗暴的。 其一、权力形成的凝聚力不太适用于经济类、文化类组织;其二、权力依靠强制力和恐惧来推行,必然招致人性的反抗。秦王朝就是一个试图单纯依靠权力与制度维持组织战斗力的反面样本,只有强力,没有利益分配和情怀信仰,更没有亲情人性。结果如何呢?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秦如此,项羽也是如此。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说的很清楚了:项羽失天下,“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仅有利益分配、物质刺激的组织也是捉襟见肘的。 没有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任何组织都难以在激烈的竞争中留住人才,保持自己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但只注重物质刺激的管理,组织凝聚力也难以持续。其一、物质刺激存在着“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单纯增加员工的收入,在初期比较有效,后期收效则逐渐缩小;对底层员工比较有效,对中高层资深员工则效应递减;其二、“这山望着那山高”,总有一些竞争对手给出的价码比你高。试图用高薪作为激励员工的终极武器,会陷入“不涨薪不行,涨薪也不行”的尴尬状态。某顶尖通讯公司在业内以高薪、期权和股息著称,可以说战斗力凝聚力都很强了。但因为超高强度的加班“狼性文化”,频频爆出“高龄”员工被变相辞退新闻,至于员工过度竞争导致的抑郁自杀或者离职现象也时有耳闻。可以说很好诠释了什么叫做“别把公司当成家”了。 仅有情怀和念想的组织也是难以持久的。 千万不要低估情怀和念想的力量,看看创业初期的太平天国就知道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人不饱暖,”“四海皆兄弟”的“天国创业梦”,曾一度激起员工多大的战斗热情!短短两年从珠江到长江,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与清政府南北对峙分庭抗礼。但,也不要高估情怀和念想的后续力量。定都天京后,曾经的革命情怀让位于争权夺利,昨天的平等许诺让位于等级特权。一场天京内讧更是无情撕裂了天国梦的虚妄无力。无数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教训都告诉人们简单的事实:当情怀遭遇房价阻击,当理想遭遇现实嘲弄,能坚持情怀、拥抱理想的永远是少数。理想主义固然指引方向鼓舞人心,经验主义才是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出路。理想主义负责提出问题,但解决问题却只能用经验主义。一百年前的年7月20日,胡适先生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乌托邦的价值在于引领和批判,而绝不应当是用权力推行,凡试图在人间建立天国的,无不最终筑成了监狱。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痛定思痛的顾准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仅有感性亲情的组织是天真脆弱的。 在组织中营造轻松和谐的人际氛围当然是愉悦的,但组织并不是“家”。现代组织的演进方向是“去家庭化”“去血缘化”。家庭血缘组织的亲情原则不适用于大多数现代组织,情感很容易瓦解组织的纪律边界。“任人唯亲”扼杀“任人唯贤”“任人唯能”在不少组织中已见惯不惊。“人人都是单位的主人翁”其实模糊了现代组织的清晰分工。改革开放之初诞生的乡镇企业大多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儒家传统的人伦精神又天然助长“用自己人”的裙带之风。人情化血缘组织无法与国际规则、法制规则、市场规则对接,不少曾笑傲江湖的家族企业在新世纪中折戟沉沙也屡见不鲜了。所谓现代企业,其实就是现代组织。 (五)学校是个什么组织? 学校这个组织很有意思。学校是社会上所有其他组织类型的袖珍模板。可以说,学校是未来社会各种组织的“孵化器”。学校这个微型“组织孵化器”的运作模式,将是孩子们建构成人世界真实组织的母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先生说:“我们留给子孙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 这句话也可以继续推演一下: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取决于我们在世界上建立什么样的学校。我们建成什么样的学校,取决于学校这个组织的模样。 学校该是什么样?学校不该是什么什么样? 政治学家阿克顿勋爵说过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结论也适用于学校。当然,在学校里,所谓“权力导致的腐败”不一定是通常意义上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而是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模式导致的对人性本身的伤害。权力本位的学校是监狱化组织,监狱化组织的特点是全方位无死角管控,监狱化的学校留给世界的子孙只能是奴隶的模样,奴隶们只能建设一个奴隶社会,因为奴隶唯一的梦想是成为奴隶主。案例:安徽怀远一小学某班副班长,利用检查作业、监督背书等权力,在两年内逼迫班内同学上贡两万多元。 利益本位的学校是商业化组织,商业组织的最大目的是牟利,牟利化的学校留给世界的子孙就是市侩的模样,市侩建设的只会是牟利的自私社会,因为市侩的唯一梦想就是发财。真实案例:某资深教师考前为学生串讲高考考点,听课的某同学将老师讲课的内容制作成音频,然后放到网上贩卖,据说获利不菲;笔者送毕业班时为考生整理的原创内部资料,被部分“头脑灵活”的考生在高考后批量翻印,在各中学门口摆摊贩卖。美其名曰“勤工俭学”“助力学弟学妹”。钱理群教授曾高声疾呼:名校正在批量制造“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看来钱老还是低估了功利主义教育的杀伤力,当下的某些莘莘学子,哪里还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啊,他们早已懒得伪装了,早已迫不及待蜕变为“粗鄙的利己主义者了”。看看最近爆出的金融圈恶俗饭局中的某名校美女,还有高铁霸座的某博士,不难略窥一二。 学校的使命是文化传承,学校的唯一目标是育人。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当然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但现状是:以“考试”为核心的教育模式愈演愈烈,绝大多数中小学从“学校”变成了“考校”,老师从“教书”变成了“教考”,“学生”也变成了“学考”。国家提出“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正是对教育弊病的精准矫正。可当下,“立德”让位于“立分”,“树人”难免被狭窄化。症结在于,惨烈单一升学竞赛模式之下,“全面发展”阉割为“片面发展”、“片面发展”简化为“考试训练”。“考试”本身不是错,是实现教育目的重要测量手段,但过度、过量、过密的纯应试,将教育手段倒置为教育目的,必然导致大批量的学生厌学、老师厌教、家长厌校。当学生离开学校之日,就是逃离读书之时,这就是教育与学校的异化了。 理论上讲,孩子教育是家庭、学校、社会、同伴、自我五个因素的合力。可现实是,一说到教育,似乎就只剩下讨论学校和家庭的责任。尤其是一出问题,就是学校老师的问题。 原因在于:在社会、体制、学校、家长的合谋下,学校教育霸权的过度扩张。 现在学校教育堪称“越位”,对学生管的太多,太具体,过度教育、过度学习、过度管控,学生在校是全面的身心管控,时间精确到分钟,行为精细到上厕所次数;学生回家是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基本每天都熬夜到凌晨,并随时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ianyingjiea.com/dyjhb/11742.html
- 上一篇文章: 少女要求下架性侵影片遭拒同学亲友数十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